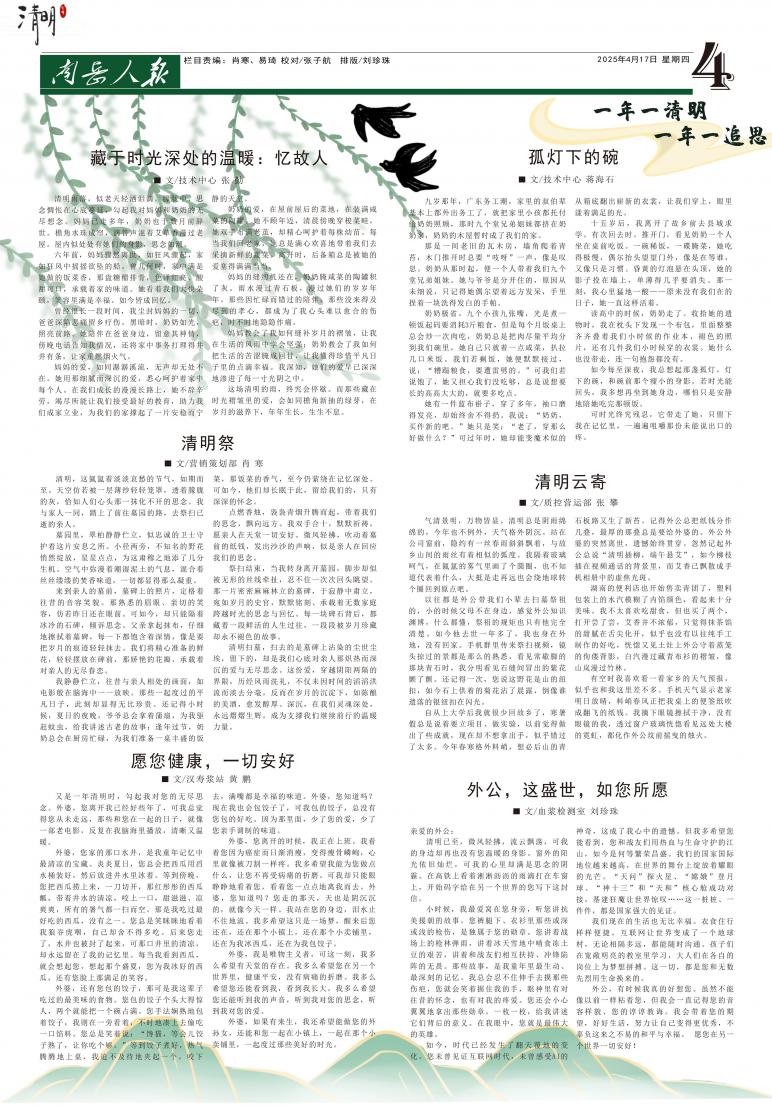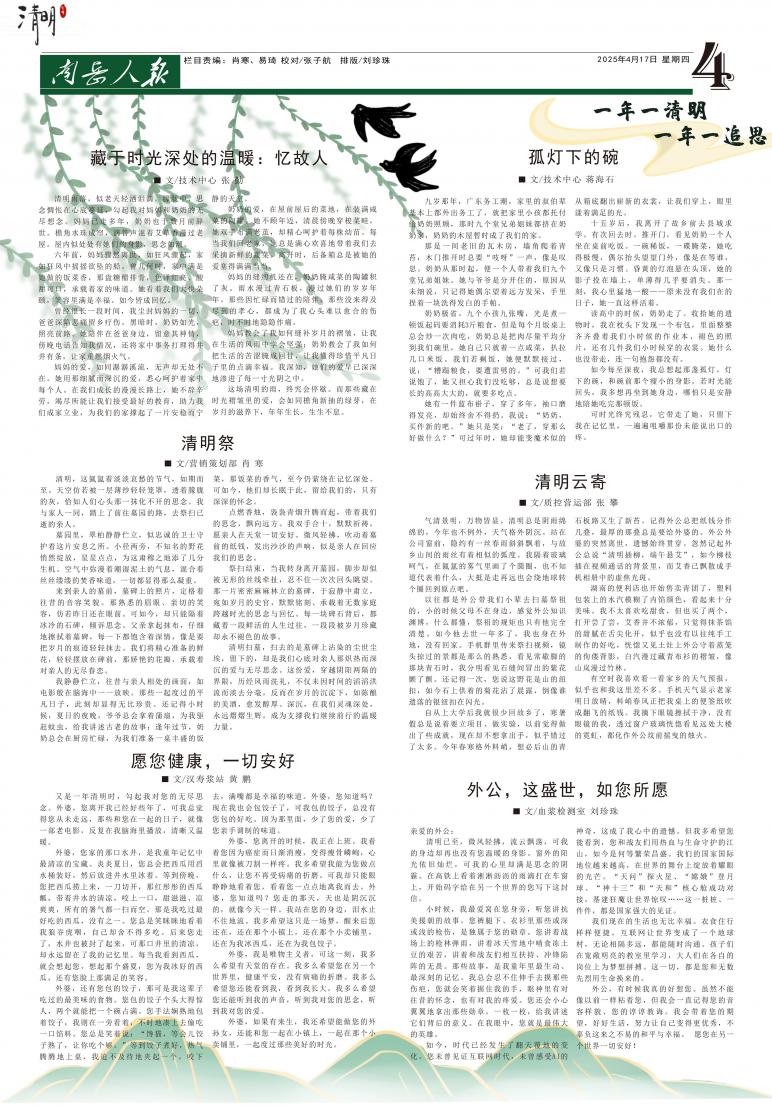
A04:版面四
孤灯下的碗
文/技术中心 蒋海石
九岁那年,广东务工潮,家里的叔伯辈基本上都外出务工了,就把家里小孩都托付给奶奶照顾,那时九个堂兄弟姐妹都挤在奶奶家,奶奶的木屋暂时成了我们的家。
那是一间老旧的瓦木房,墙角爬着青苔,木门推开时总要“吱呀”一声,像是叹息。奶奶从那时起,便一个人带着我们九个堂兄弟姐妹。她与爷爷是分开住的,原因从未细说,只记得她偶尔望着远方发呆,手里捏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手帕。
奶奶极省。九个小孩九张嘴,光是煮一顿饭起码要消耗3斤粮食,但是每个月饭桌上总会炒一次肉吃,奶奶总是把肉尽量平均分到我们碗里,她自己只就着一点咸菜,扒拉几口米饭。我们若剩饭,她便默默接过,说:“糟蹋粮食,要遭雷劈的。”可我们若说饱了,她又担心我们没吃够,总是说想要长的高高大大的,就要多吃点。
她有一件蓝布褂子,穿了多年,袖口磨得发亮,却始终舍不得扔。我说:“奶奶,买件新的吧。”她只是笑:“老了,穿那么好做什么?”可过年时,她却能变魔术似的从箱底翻出崭新的衣裳,让我们穿上,眼里漾着满足的光。
十五岁后,我离开了故乡前去县城求学。有次回去时。推开门,看见奶奶一个人坐在桌前吃饭。一碗稀饭,一碟腌菜,她吃得极慢,偶尔抬头望望门外,像是在等谁,又像只是习惯。昏黄的灯泡悬在头顶,她的影子投在墙上,单薄得几乎要消失。那一刻,我心里猛地一酸——原来没有我们在的日子,她一直这样活着。
读高中的时候,奶奶走了。收拾她的遗物时,我在枕头下发现一个布包,里面整整齐齐叠着我们小时候的作业本、褪色的照片,还有几件我们小时候穿的衣裳。她什么也没带走,连一句抱怨都没有。
如今每至深夜,我总想起那盏孤灯,灯下的碗,和碗前那个瘦小的身影。若时光能回头,我多想再坐到她身边,哪怕只是安静地陪她吃完那顿饭。
可时光终究残忍,它带走了她,只留下我在记忆里,一遍遍咀嚼那份未能说出口的疼。